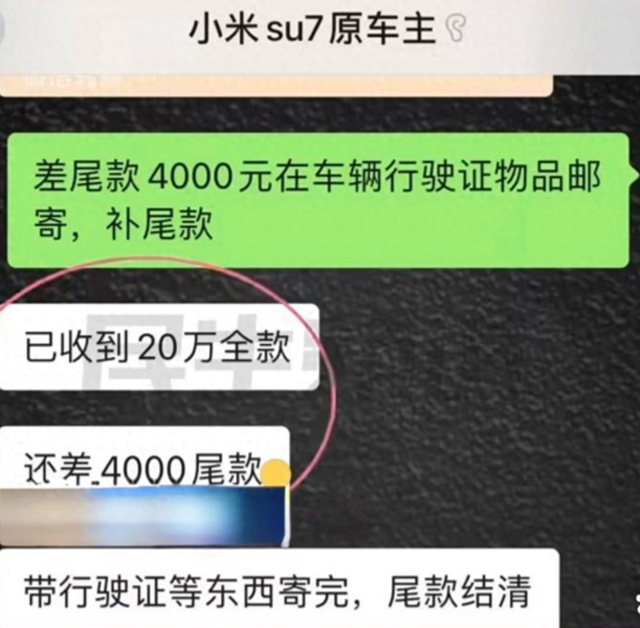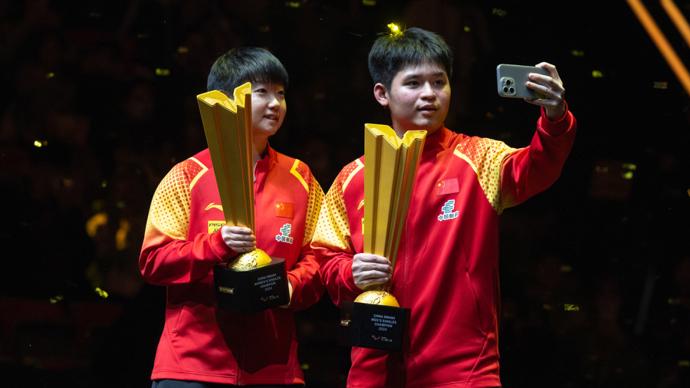童年时期,父亲时常因为工作不在家,母亲难免有事要外出,记忆中,我在南部老家四层楼高的透天厝里,度过了许多独自守家的夜。犹记得,每当母亲出门前,总会叮嘱某些事情,然后我会看着她的眼神点点头,目送她离家的背影,并透过落地玻璃门的缝隙,竖起双耳聆听她骑车远去的声音。
对分离的不安,来自亲子关系中不稳定的依附。
在那个幼时的记忆里,时间对我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即使看着时钟的长短针交错走过,仍然无从判断,时针落在何处,才是母亲回来的时机,只能凭印象估算母亲究竟出去了多久。
但自我的主观感觉是抽象且不可靠的。比方说,母亲才出去半小时,对当时不安渺小的我而言,却好像有一种看不到时间尽头、需要无尽等待的恐慌。所以我常常在母亲出门后,朝着她离开的方向跪地双手合十,低着头呼唤我所知的各方神灵、菩萨、上帝:“不管是什么神啊!求求你们,请让我妈妈一路平安,别出意外。”我常常这样边呼唤,边哭泣,直到听见母亲的摩托车声在巷口响起,才赶紧收起眼泪,装作没事地迎接她进门的身影。

学了心理学之后,我才明白这种对分离的不安,来自亲子关系中不稳定的依附关系,而那种一分离就仿佛死亡即将降临的恐慌,可能是传袭自家庭的阴影。

成年后,我花了很多时间认识自己,并且探索父母的故事与处境。我逐渐理解:如同我这样等待着母亲,母亲也如此等待着父亲。身为警察眷属的母亲,从小就生活在“父亲离家出勤,母亲胆战心惊”的状态中,所以当她遇上随兴不羁、工作需要喝酒应酬,又常得自己开车的丈夫,童年时的心理状态在婚姻中便转换成:丈夫出门应酬,妻子胆战心惊。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我自然从小就嗅出这样的氛围。虽然我不曾与父母谈论过,但那些过去的印象、每个瞬间在父母脸上闪过的表情,早已如同烙印般刻画在我心底,左右着我的情感,也影响着我成年后的性格。
所以,在别人面前,我看起来总是坚强的,更年轻时的我,性格甚至非常刚强。走过心理分析之路,我才渐渐理解自己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预备这个世界上可能只剩我一个人的日子。母亲也因为活在潜在的死亡焦虑中,出门时总会叮嘱我,她和父亲的死亡保险单放在哪里。

因此,那个跪在地上无助地呼唤神灵的我,逐渐长成坚强面对生离死别的我。但其实,许多情绪和感受,我早已习惯一个人默默消化。
面对镜头的恐惧,来自怕被看透的不安。
在发现自己总是默默承担感受之前,我一直游走在“冷静乖巧”及“直率冲动”之间(要知道,这两者是我童年时赖以生存的要件)。我在这种双重情感的夹攻下常常觉得难以呼吸,所以常常混在人群里,透过喧闹的谈笑声,忽略自己内在的矛盾。
童年时独自在家的夜晚,我看了不少文学作品。我常趁父母不在的时候,溜到楼与楼中间的夹层,在父亲的书房里找个阴暗的角落,在昏黄的灯光下,偷偷翻阅书柜里那些泛黄的老书,伴着远处地下室传来的蟋蟀叫声,在偌大的房子里,静静咀嚼小说中的故事情节。

在成为心理咨询师之前,我其实是个就读中文系的大学生,爱文学、电影,喜欢独自唱歌、在舞台上演戏。我曾经以为自己会成为一个表演工作者,诠释所熟知的故事情节,或者将心理矛盾分裂的情感投射在舞台上。
直到大四的戏剧课,老师发现我有“眼神聚焦”的困难——我没办法把眼神放在一个定点上好好地说话和演戏。我甚至发现自己面对镜头有困难,但后来我竟然成为需要上媒体面对镜头的人。
学了分析心理学后,我不断寻求自己面对镜头恐惧的答案。我发现,镜头之于我,就像眼睛。我感到困惑:难道是怕被看透什么吗?是的,现在我终于可以承认:我真的很怕被看透。外表看似坚强的我,内心其实充满不安。
比起害怕被不相干的人看透,我更害怕被认识的人看透。直到现在我终于明白,这种害怕是怕他们失望,而这个“他们”,正是我的父母。
“如果他们一定得出门,我又怎么忍心让他们担心家里这个其实一点也不坚强的独生女儿呢?”这是埋藏在我心底最深处的声音。

人际关系不顺利,是因为我们都得了“父母病”。
诚实以对,自我坦承后的觉察,一开始并没有让我比较好过些。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活在对父母的怨怼里:我生气他们没有给我任何手足,怨恨他们不经意的缺席制造了我的孤单。于是,我引爆许多冲突:离家、叛逆、对父母大吼……直到发现,原来我染上了“父母病”——把问题统统推到父母身上,以为自己没有问题,却往往在与父母的关系中留下更多口是心非的遗憾。染上“父母病”的我们,常常对父母感到失望和生气,抱怨童年的缺失与渴望,但这样的情绪往往让我们体会不到真实的自己,也看不到真实的父母。
我从2007年开始在心理咨询领域学习,逐渐从个人咨询转向家庭治疗,在长期的家庭治疗实务工作中,听过形形色色的家庭故事。直到2013年,我再度把焦点从家庭转到个人身上。我想,这都是为了治愈自己身上的“父母病”,才展开这段与父母的和解之路。
如果可以,我们也许能相互陪伴,一起踏上这场疗愈之旅。这可能会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