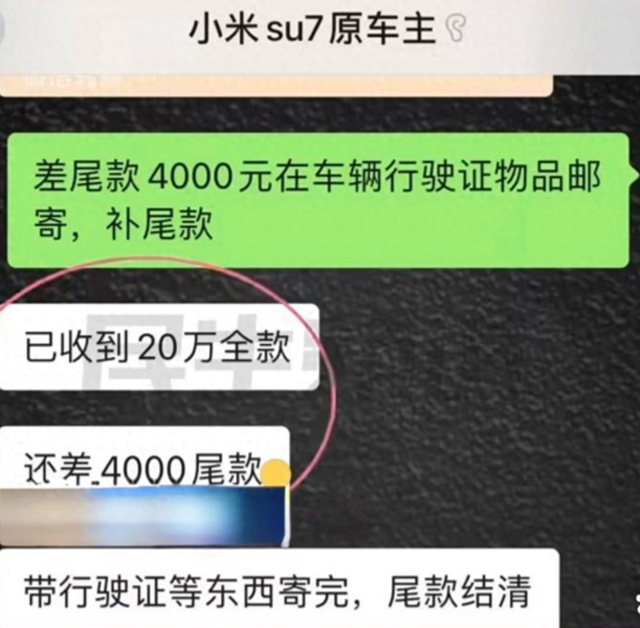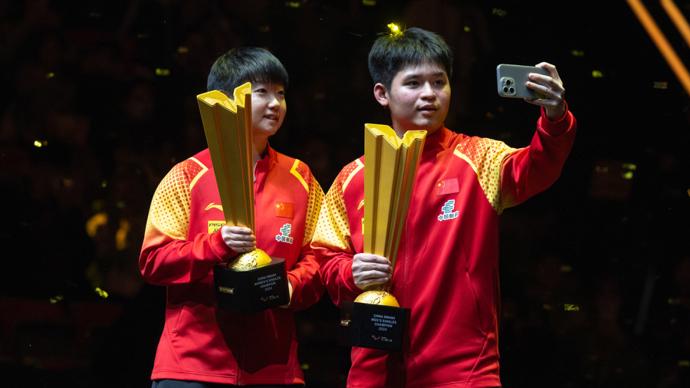撰文 | 田为
来源 | “医学界”公众号
意大利著名医史学家阿尔图罗·卡斯蒂廖尼在《医学史》中写道:“医学是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份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诞生的。”樊碧发从心底里认同这句话。
从一名麻醉学研究生,到成为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第5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和第8届候任主任委员,樊碧发的职业生涯和我国疼痛学科的发展息息相关。
他说:“医学和解除疼痛密切相连,医学的最高目标是解除人类痛苦。不了解疼痛,就不能深刻地理解医学真谛;要想对医学有深入的理解,必先从了解疼痛开始。”
可能是先天的爱好
樊碧发是山西医科大学1979级的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一开始,他并没有对哪个学科产生特别的兴趣,心里只想着好好学习。
后来,他逐渐发现了麻醉学的神奇之处,“外科的进步实际上和麻醉学的进步有很大关系,假如没有麻醉,患者无法忍受手术带来的痛苦,连切阑尾这种小手术都做不下去”。于是,他决定报考麻醉学的硕士研究生。
疼痛学和麻醉学有重合的地方,镇痛是麻醉的部分目的所在。通过学习,在中国医科大学攻读麻醉学硕士的樊碧发得知了疼痛这门科学,他萌生了成为一名疼痛医生的念头,“可能就是先天喜欢吧”。
1989年5月,原国家卫生部印发《关于将麻醉科改为临床科室的通知》,确定麻醉科为临床一级诊疗科目的同时,将疼痛的诊疗与研究也纳入了业务范围,为麻醉科医生在临床上实践疼痛治疗创造了条件。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疼痛科的起步期,很多医院的麻醉科医生开始开设疼痛门诊,樊碧发是最早尝试的一批。1989年7月麻醉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日友好医院麻醉科工作。同年,他向医院申请开设疼痛门诊。
最初的疼痛门诊很简易,甚至连个像样的诊桌也没有,日接诊量也不算多,“一天多的时候也就十来个病人”。樊碧发回忆道:“大医院里总有些受疾病折磨、痛苦难忍的患者,可能转来转去,看到有个疼痛门诊,就来了。”
来就诊患者的情况大多相似——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疼得要命;顽固性神经痛、骨关节痛,吃药没效果,做了手术也还是疼。除此之外,还有癌症引发的疼痛。

他印象最深的一位患者,是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家就住在中日友好医院对面的小区里,“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了,跟我说他走不了几步路就疼得厉害,问我能不能给他治治”。
樊碧发判断老人是“老寒腿”,也就是现在的骨关节炎。按照膝关节腔内外联合疗法,樊碧发为其治疗了一个疗程大约3次。疼痛慢慢减缓,到最后,老人走路时不再需要拄拐杖,也能出门买菜了,生活质量得到很大提高。
“他非常高兴,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把他的疼痛控制以后,他们小区一堆老头老太太‘闻风’过来看病,我也都治得差不多,心里很有成就感。”樊碧发笑着说,“老百姓认可你,认为你能解决病痛、找你看病的热情,是支撑我往前走的最大动力,如果没人来看病,(这件事)肯定做不下去。”
就这样,中日友好医院的疼痛门诊慢慢有了口碑,多的时候一天能有二三十个患者,出诊医生也发展到四、五位。但有的患者的疼痛十分顽固,临床实践让樊碧发意识到,老百姓有大量且普遍的解决疼痛的需求,而自己仅凭业余时间里学习的那些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为此,20世纪90年代间,他先后两次前往日本进行疼痛学研修,之后也时不时去各个国家开会、学习、与同行交流,引进新的理念和技术。“我们跟国际上的交流从来没有中断过,即使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会在线上沟通。”他说。
后来,樊碧发出任中日友好医院麻醉科的副主任,对疼痛门诊和出疼痛门诊的医生进行管理,直到2003年,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成立。
“医院觉得既然患者有这方面需求,我们的发展势头也很好,就把我们从麻醉科里独立了出来。独立之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床位,有志于疼痛的麻醉医生也从麻醉科转入疼痛科,走上更专业化的道路,我们的发展速度就更快了。”他说。
中国有了疼痛科
疼痛也是一种疾病,这个理念直到21世纪才开始被医护人员广泛接受。如今,疼痛已被确认为是继呼吸、脉搏、体温和血压之后的人类第5大生命指征。

现代疼痛治疗起源于美国。1961年,著名麻醉科教授Bonica在华盛顿大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临床疼痛中心。次年,日本东京大学麻醉科教授山村秀夫在东京大学创办了日本第一个“疼痛外来”,国际现代疼痛诊疗从此逐步走向世界。
相较国外,我国的疼痛学起步较晚。1989年由北京大学韩济生院士牵头创建的中华疼痛研究会(CASP),于次年成为国际疼痛学会(IASP)中国分会,并在1992年转为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在2020年12月20日结束的最新一次换届选举中,樊碧发当选第8届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此前他曾担任过第5届主委。
疼痛学具有多学科特点,神经内、外科,骨科,肿瘤科,康复科等多个学科都有疼痛治疗的需求。但疼痛学并非临床各个学科的简单相加,需要专业人才,从疼痛的机理(包括解剖生理学、动物实验等)、临床试验、临床诊断和鉴别诊断、治疗方案、康复和预防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探索。换言之,即“走专科化发展道路”。
在韩济生院士的带领下,经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多方呼吁,2007年7月16日,原国家卫生部发布卫医发【2007】227号文件,确定在《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中增加“疼痛科”为一级诊疗科目,我国二级以上医院均可开展疼痛科,标志着我国疼痛科正式建科。
在疼痛科成立初期,人员编制、职称晋升、收费项目等方面均存在问题,医教研体系也未打通,学科发展面临很多困境。
以中日友好医院为例,据樊碧发介绍,“虽然医院很重视疼痛科,我们在医院里和其他科室也处于同等地位,但因为全国层面还没有疼痛科的职称晋升体系,疼痛科医生想职称晋升,就得借助其他科室的职称晋升,非常麻烦”。
为了开辟学科人才成长路径,稳定医师队伍,在原国家卫生部人事司、中华医学会的支持下,2008年和2012年,原卫生部卫生人才中心相继开展了国家疼痛医学专业中级、高级职称考试,打通了疼痛科的职称晋升通道。
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樊碧发还发现,学科要有规范的医疗收费项目,才可能持续性发展,“没有收费项目,我们就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治疗,或者做了工作但却得不到相应的报酬,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临床业务水平的提升”。

首先要对医疗技术进行立项,确定能治什么病、能用哪些手段进行治疗,最后形成疼痛科医疗技术服务收费标准。在我国医疗技术目录中增加疼痛诊疗技术科目,是2008年以来,樊碧发作为国家疼痛科诊疗项目立项工作组组长,一直在坚持推进的工作。
“有了收费项目还不够,要有医保报销,老百姓才能受惠。我们一开始遇见过很多老百姓,一听说治疗要自费就算了、不治了,这也限制了学科在临床上的发展。所以我们积极与医保部门沟通,在医保部门的支持、帮助下,逐步把一些基本的治疗项目纳入了医保。”他说。
还有《中国疼痛医学杂志》《中华疼痛学杂志》(原《实用疼痛医学杂志》)的编辑出版,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组织编写的《临床诊疗指南(疼痛学分册)》《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疼痛学分册)》……在疼痛科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樊碧发都是参与者乃至力推者。
疼痛科的发展永无止境
从疼痛科的追随者、探索者到引领者,一路走来,樊碧发付出了很多。他坦言,在疼痛科发展的早期阶段,同为麻醉科医生,他的收入几乎是科里其他医生的一小半,“因为醉心于疼痛诊疗,我就很少做临床麻醉了”。
“实际上我那时候也很年轻,有很多经济方面、生活方面的压力,非常幸运的是家人很支持我,”他说,“没有情怀和毅力是没法坚持的,咬着牙坚持下来之后,发现推动了疼痛科事业的发展,撑起了一片蓝天,就觉得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樊碧发几乎全年无休,每天早上六点前起床,到晚上12点多才休息。他有繁忙的临床工作,教学和科研任务,及国内外学术交流与技术合作等工作。有时候周末待在家的时间长了,孩子都觉得奇怪,“你今天怎么在家?”
在以樊碧发为代表的疼痛科医生的努力下,中国疼痛学的发展如今受到了世界关注,这让樊碧发十分骄傲,“日本的疼痛学曾经很领先,当年我去日本开会、学习、参观,跑了很多趟。现在日本同行认为他们的疼痛医学被中国超越了,要向我们学习。因为我们走的是专科发展道路,日本国会还专门开了疼痛论证会,讨论日本要不要也设立疼痛科”。
韩济生院士在庆祝我国疼痛科成立十周年的会议上致辞时也提到了这件事——“2016年在日本举办的第16届世界疼痛大会首次有了中国专场报告。值得提及的是,在日本参加会议期间,樊碧发教授被邀请到日本的国会做报告,介绍中国疼痛医学的发展现状及进一步发展趋势,引起日本疼痛学界及政界的重视,明确表达了借鉴中国经验的愿望。”
作为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在中国发展了不过30多年的疼痛学,还是面临很多挑战。樊碧发提到,在科研方面,尤其是有巨大影响力的原创的科学技术研究方面,我国疼痛学科至今仍未取得太大建树。
在人才培养方面,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很多大学的医学通科教育还未将疼痛学列入其中。尤其在专科人才培养方面,完善医学教育体系,建立国家层面的疼痛专科医师培训制度,也需要进一步推动。
还有面向公众的疼痛学健康教育,让老百姓获得正确的疼痛学知识,提高健康意识……
“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做的事情越多就越显得我们生机勃勃。”樊碧发说,“我们不用着急,一点点地发展就好,疼痛科的开山鼻祖韩济生院士经常说,为民除痛是一条路,永远没有终点。”
参考文献:
1.韩济生.中国有了一个疼痛科—庆祝疼痛科成立十周年大会讲话
2.樊碧发.疼痛建科,跨越发展,新兴学科,大有可为——写在疼痛建科7周年
3.巴衣尔策策克.北京地区疼痛科室建设现状
4.樊碧发.疼痛医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5.《生命时报》:“疼痛科大咖”樊碧发:吃得了苦,但没必要忍得了疼
6.高崇荣,陈金生.谈疼痛科的建设与发展